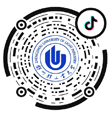11月21日,河南日报分别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发展历史学科的理论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宋代榷场贸易中的展现》《地理密码: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然根基》为题,报道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文章。原文如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对发展历史学科的理论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家统编教材,它将政治性与学理性、专业性与通识性、共同性与差异性紧密结合,创造性阐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概念及内在关联,集中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演进的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作为泛义上的史学教材,《概论》对发展历史学科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正确史观、重构了叙事范式、丰富了研究内容三个方面。
确立历史学科的正确史观
中华民族历史观是指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内在价值与规律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蔽除了唯心史观的影响、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权威地位,是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基础和主线,也是贯穿《概论》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始终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的“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揭示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科学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自觉”到“自立”“自强”的演进逻辑,为历史学科发展提供根本遵循。《概论》在历史观方面采用“破立并举”的方式进行阐述。“立”就是用“五个共同”的唯物史观科学论证地理与文明、国家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确证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史实和发展必然。“破”就是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批驳“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观”“赞米亚学说”等错误历史观,深刻揭示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实体”,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概论》在历史观上的“破立并举”,为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
重构历史学科的叙事范式
传统中国史研究主要分为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三类。通史一般以单维度历史记述为主,侧重于中国历史各个阶段的连续性和贯通性;断代史重在记述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书写体例突出时代或朝代的独特性;专门史通常是对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民族史等的记述,侧重于专门化研究。《概论》不同于以上三类历史研究,它从中华民族的整体视角出发,紧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轴,站位百万年的人类史、上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呈现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共同性”增长和各民族融聚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打破了以政治史为主轴的王朝断代史和族别关系互动史的传统历史叙事。从范式上看,《概论》不是简单的“记述历史”,而是将分散的族别史、区域史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演进逻辑,以“共同性”为锚点、以“大一统”为基线,描述、阐释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从叙事逻辑上看,史前各族群在生产生活中不断互动、融聚,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群,创造了早期中华文化圈;夏商周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形成,维系了“天下”秩序和华夏共同体;秦汉时期政治“大一统”理念、制度的确立,构建了“中原—边疆”的有序治理格局;北魏孝文帝改革展现了游牧民族主动融入中华的历史自觉,为隋唐“大一统”奠定基础;辽宋夏金“共奉中国”,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聚性发展;元明清时期“混一南北”“中外会通”“中华一家”的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统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基本指向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各民族、各区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进步、大繁荣景象。这种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历史叙事方式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必将促使历史学科发展从“民族视角”向“共同体视角”加速转换。
丰富历史学科的研究内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重视历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概论》的编写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体现,关系到教育引导各族人民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从起源、扩大、发展,到最终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如何准确理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融聚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历史史实;如何科学把握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突出特性。《概论》既关注各民族的独特发展轨迹,又聚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在坚持解答理论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突破,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史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同时,《概论》还构建了多维史料框架,既有史前考古学史料,也有古代文献学、考据学史料,既有近现代档案学史料,也有区域国别史料,各方面史料的贯通使用,极大扩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史学研究的张力。《概论》在考证、使用史料时,不仅注重挖掘史料蕴含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旨,更注重史料选择的价值导向,强调优先挖掘那些能够印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彰显统一多民族国家特质的史料内容。这就从根本上规制了历史学科在史料选择上的内容偏差与价值偏差,让历史叙事更具政治性和科学性。
综上,《概论》既是一部全新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首部中华民族共同体通史,其出版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史料体系的基本形成,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学科的研究内容与视域。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宋代榷场贸易中的展现
榷场互市是宋代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和渠道,各民族在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经济共同体,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
宋代榷场的形成与沿革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族、诸政权即存在贸易往来。榷场是辽宋夏金时期在边境地带与邻国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所。据《金史·食货志五》记载:“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汉书·景十三王传》韦昭注有:“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榷”意味“专卖”“专利”,即官府专卖,小民不得私自经营。宋辽之间很早就有边境互市。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于镇州、易州、雄州、霸州和沧州等州“各置榷场”,辽于涿州新城、振武军和朔州城南置榷场,进行官方贸易。后因范阳之战,罢互市。宋景德二年(1005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后,才正式确定榷场之制,并“固守盟好,互市不绝”。中原与党项的互市贸易早在西夏建立前就已经开始了。宋景德四年(1007年),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元昊反叛宋朝后,宋废除了保安军榷场,诏令陕西、河东等地不得与党项人互市贸易及至西夏立国。元昊臣服后,宋朝才又在保安、镇戎两个屯兵处设置榷场。但由于宋与西夏关系时好时坏,榷场互市也是废置不断。宋宣和七年(1125年),源自黑水靺鞨后裔的女真族大败契丹族,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西迁建立哈喇契丹(也称黑契丹),从此金取代了辽在北方的统治,辽宋之间的榷场互市随之转向金宋。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与金议定了“绍兴和议”,两国在西起秦州、东沿淮水的分界线上广设榷场,其中淮水北岸的盱眙场和南岸的泗州场是双方的交易中心。宋在四川边疆、荆湖南北路边境、广南西路边境的各州军开设众多的互市榷场,与南方和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互市。在官方主导的榷场贸易开展的同时,民间走私活动也呈现更为频繁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是正常贸易的交易税率过高、官方对正常交易商品的限制严格且频繁变更,加之连年战争致使商道不畅,致使出现宋“禁人私贩,然不能绝”的境况。
宋代榷场贸易的特点
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多政权的并立,榷场贸易成为各政权维持一定经济联系,进而维持自身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宋代的榷场贸易具有政治博弈功能。宋以前,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主要有和亲和羁縻两大类。辽宋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依靠血缘关系维持对社会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而宋在军事上的弱势,又无法为羁縻政策提供强大的武力保障。这一时期,两项民族政策得以维持的基础不复存在,宋需要寻求新的政策以平衡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榷场贸易则成为新政策体系的映射。这一时期的榷场贸易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流,更成为各政权间政治关系的晴雨表,其废与兴往往与政权间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密切相关。每当发生战争时,宋通过停止榷场贸易逼迫对方就范。宋仁宗庆历元年至二年(1041—1042年)西夏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后,宋停止岁赐、关闭与西夏的互市,造成西夏境内“茶无饮、衣帛贵,国内疲困”的局面,迫于压力,夏宋签订庆历和议,重开榷场,恢复贸易往来。宋代榷场贸易物品具有严格限制。榷场贸易作为官方认可的经济互动形式,其物品交易种类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体现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分工。但这一时期的榷场贸易物品类型是有严格限制的。例如:宋对辽严禁私市硫黄、焰硝、炉甘石、水银等,辽严禁向宋输出马匹。
宋代榷场贸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化的影响
宋代榷场的设置,助推了辽宋夏金各区域经济的融聚。榷场贸易下形成的商贸网络不仅丰富了各政权诸族群的经济活动,也增强了彼此间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夯实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经济基础。宋代榷场的设置,为政治整合提供深层力量。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藩篱,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宋代榷场的设置,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以榷场为载体的贸易往来带动文化互鉴与生活习俗交融,打破心理隔阂,催生跨民族信任。同时,榷场维系边境和平,推动多民族杂居与协作,从经济、文化、社会层面加速民族融合,成为宋调节民族关系的关键纽带。这一历史时期,除宋外,辽与西夏、回鹘,金朝与高昌、吐蕃等均有榷场互市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不仅增强了各族群的经济往来,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以致出现了“宋有名作问世,辽必锐意搜求,并刊刻流布”的情况。由经济互补到文化认同,由文化认同到情感共鸣,绵延数百年的宋代榷场互市为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应有贡献。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权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为元明清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辽宋夏金时期榷场贸易的繁荣也充分证明,政治上的暂时分裂并未割断各族间的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民族在互融共生中共同缔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地理密码: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自然根基
当我们回望人类文明的长河,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原生文明如星辰般璀璨却先后陨落,唯有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始终绵绵不息、薪火相传。这一独特的文明连续性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密码?中华文明的地理禀赋,正是稳定与多样的辩证统一。稳定的外部环境保障了发展的连续性,多样的内部结构增强了抗风险的韧性,二者共同铸就了文明延续的自然根基。
复杂地理结构中华文明的“天然屏障”与“内部沃土”
从空间格局看,东亚大陆被天然地理屏障层层环绕:东部的太平洋形成难以逾越的蓝色疆界;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构成陆上阻隔;北部的蒙古高原与西伯利亚冻土带限制了大规模外敌南下;南部的云贵高原与南海诸岛,热带丛林与海洋同样形成自然防线。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并非完全隔绝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而是在人类早期生产力有限的条件下,有效降低了大规模外敌入侵的频率与强度,为文明的独立演进与内部整合提供了安全缓冲。
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内部广阔的地域与多样的地形,为早期文明的萌发提供了丰富的“试验场”。从东北平原的黑土地到江南丘陵的红壤区,从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到四川盆地的沃野千里,平原、山地、盆地、河谷等地形交错分布。不同的地理单元孕育出多样的生存方式:华北平原的平坦开阔适合大规模农耕,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密布催生稻作文化,黄土高原的沟壑地形发展出独特的旱作农业体系,西南山地的垂直气候带则保留了采集渔猎等多种经济形态。这种内部多样性使得文明的火种能在不同区域独立点燃,又通过河流与陆路相互联系,形成“和而不同”的文明共生格局。
气候突变的“文明考验”从“多元”到“一体”的地理逻辑
约1.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暖期,全球气温回升,东亚大陆降水增加,冰川融水补给河流,森林与草原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地理与气候的双重优势,催生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满天星斗”式起源模式。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数百处文明遗址如星辰般散布在东亚大陆,覆盖了从寒温带到亚热带的广阔区域。
然而,距今4200年前后,地球经历了一次以“南涝北旱”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性气候突变:低纬度地区降水异常增加,高纬度及内陆地区则陷入持续干旱,这对依赖稳定生态环境的早期农耕文明构成了严峻挑战。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因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量锐减,绿洲农业系统崩溃,苏美尔城邦陷入饥荒与战乱,最终被北方游牧民族取代;北非尼罗河流域降水减少导致尼罗河泛滥周期紊乱,古埃及古王国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因粮食短缺瓦解,进入了长达百年的“第一中间期”黑暗时代。
同一时期的中华大地,“满天星斗”式分布的区域文明也遭遇重创。黄土高原北部的石峁文化,因水土流失与持续干旱叠加,脆弱的旱作农业难以为继;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因南方持续洪涝陷入困境,尽管先民构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但海平面上升与暴雨引发的河湖泛滥,最终淹没了稻田与聚落。当石峁、良渚等区域文明在气候突变中相继衰落时,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却异军突起,成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核心舞台。这一“地理胜出”的背后,是中原独特的空间禀赋与资源整合能力的集中体现。
黄河中下游气候波动中的“文明抗压核心区”
从地理位置看,中原地处东亚大陆腹地,北接蒙古高原,南连江汉平原,东望海岱地区,西通关中盆地,如同文明网络的“十字路口”,便于吸收周边文化的技术与资源。地形上,中原并非单一平原,而是由黄土台塬、丘陵岗地与冲积平原构成的“缓冲带”:南部的伏牛山与大别山阻挡了南方过量的洪水,北部的太行山与黄土高原减缓了北方风沙的侵袭,中部的伊洛河、沁水等支流形成的水网,既避免了长江流域可能出现的持续洪涝,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河干流的泥沙淤积风险。
黄河中下游核心区的地理优势形成了“压舱石”效应:黄土疏松易垦的特性与丘陵岗地的防洪功能,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粟、稻、麦等农作物的多元种植与猪、牛、羊的混合饲养,构建了应对气候波动的“生态保险”。这种“地尽其用、种随境迁”的农业智慧,与黄河中下游多样的微地形相结合,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根基。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通过修建早期水利工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灌溉系统)协调水资源分配,利用黄土易开垦的特性推广粟稻混作,并不断吸纳周边文化的礼器制度与社会组织经验,从而奠定了“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空间基础。
从“山海环抱”的外部屏障到“多元一体”的内部格局,独特的地理禀赋不仅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稳定的生存环境,更塑造了其应对挑战的独特韧性。但这片土地所创造的文明奇迹,从来不只是自然的单向馈赠,更是自然与人文长期互动、共生共荣的结晶:先民们在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孕育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包容胸怀与“自强不息”的坚韧品格,将地理优势转化为文化传承的强大生命力。正如黄河与长江奔涌不息,地理基因与人文精神交织成中华文明的生命长河,让这古老的文明在岁月流转中始终弦歌不辍——这既是地理赋予的幸运底色,更是文明自身的力量,也是对“为何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这一命题最深刻的回答。
链接地址:
https://newpaper.dahe.cn/hnrbncb/html/2025-11/21/content_445_1767969.htm
https://newpaper.dahe.cn/hnrbncb/html/2025-11/21/content_445_1767970.htm
https://newpaper.dahe.cn/hnrbncb/html/2025-11/21/content_445_1767971.htm